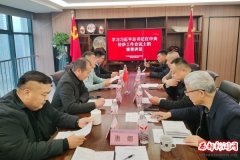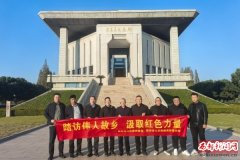(文/孔明)第一次见张立,那情景就像一幅动漫的定格。那是在我办公室,隔两张办公桌,他正襟危坐,鬈发乱蓬蓬,一副少数民族的嘴脸。不说话时冷峻,脸上棱角如版画;说话时棱角软化,抿嘴一笑,版画变成了漫画。话粗,理端正,即兴幽默,机智风趣,惹得人开怀大笑。去后好长时间未见面,但印象已不可磨灭。再见面时握手,不陌生,也不客气,就像邻居串门。他不喜客套,却做人高调;不照常理出牌,却不排斥礼尚往来;有典型的蓝田人直性子,却有收放,能屈能伸,还能迂回、拐弯。与他往来一直是循环渐进,不即不离的时候居多,却喜欢了他的情绪全在脸上。看不透他所思所想,却看透了狡猾是他的外表,敏捷才是他的如来意,大大咧咧的言谈举止使他的性情才智淋漓尽致。他主编《陕西日报》周末版时,我先后出版《谈情》与《说爱》,他都友情出手,快意作文,不吝礼赞之词。于我,这是天大的人情,足够我一生珍藏并回味。

一次聚会后分手,我一直目送了张立走远,忽然有了一种灵感,觉得张立如同一面旗幡,迎风竖立而招展。他主持《陕西日报》副刊,既有坚守,又有放弃,做主旋律文章不落俗套,与时俱进中保持了文学的本色。有这个副刊,张立被天然定位,即使脱胎换骨,仍脱不了文人这张皮,尽管他似乎回避着以文人自居。事实上,在所谓文人眼里,张立不像个文人,但在文化圈外的人眼里,张立意气用事就是个名副其实的文人。与文人不同的是抱负,是进取,是脚踏实地,是灵活机变,是狡黠中有保守,是显摆中有隐忍。与他交往有年,感觉他像一轴徐徐舒展的人生画卷,所有人生轨迹与创业规划都是亲自构思、创意、描画。他涉足过的文化产业,风生水起,绘声绘色。他像蚕,好像作茧自缚,却终于破茧而出,羽化成蝶。他有个笔名叫秦佣,于此足够暴露他的情怀与梦想:秦佣的粗犷与秦人的倔强。呶,目标在那儿,看似漫不经心,却不改初衷与方向,做人、做事都不离谱儿。在许多熟识他的人眼里,他是成功了,他起码把蓝田人张立变成了一个蓝田籍人物张立。
张立是有着文学梦想的,这梦想寄生于他的少年启蒙与青年冲动,潜移默化进而儒化了他与生俱来的性格强悍与坚硬,使他吸纳了足够的文学营养,拥有了浪漫的人生情怀,个人追求越来越明晰,个人奋斗越来有了奔头,又有了由头。他是有文学天赋的,有他的文章为证,更有他谈笑中的即兴创作为证。但文学似乎不是他的目标,而是他长途跋涉的水壶,渴饮所以能保持活力,饱吮所以心田从未荒芜。读《陕西日报》副刊,能读出他的文学情结、文学理念与文学定位,他的坚守是对文学的尊重与理解,他的放弃是对媚俗与堕落的排斥。在文学副刊日渐萎缩的今天,《陕西日报》的《秦岭》已成一道亮丽的风景,小憩其中,清新扑面,心灵骤然间安静。“耳临清渭洗,心向白云闲。”我读《秦岭》,就是这种感觉。
张立突然画画了,我一点儿也不惊奇。他浸淫书画应该不是一天两天,只不过深藏不露罢了。当他突然有了底气和勇气发表个人画作的时候,我确信他得到了天的启示与指引,他觉悟到了人生如画,画如人生。他有大阅历,对所谓艺术天地里的各色人等与粉墨登场洞若观火。他有臣服,亦有腹诽;有自信,亦有清醒;有傲慢,更有谦卑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绘画不负痴情人。他不是半路上出家的和尚会念经,他是经卷里蛰伏羽化的蛾,早成佛了。得道者天助,悟道者自助。与其说绘画是张立的人生拐点,毋宁说张立式的人生梦想需要一个栖息灵魂的港湾,在那里蓄养精神,酝酿气势,凝聚内力,饱蘸笔墨,把一生块垒都交给丹青。绘画不语,自有禅机。天聋地哑,一心一意。或许,画中张立,原本就是秦俑浴火重生。
2014年7月5日星期六